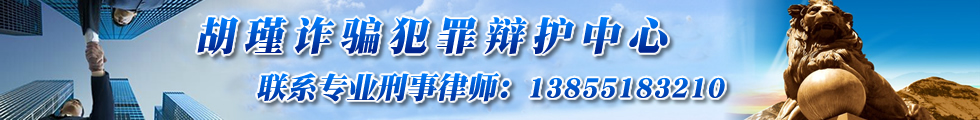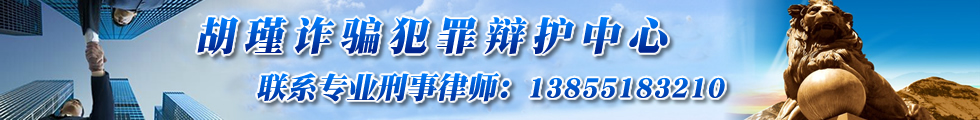“打粉”话务该当何罪,是诈骗罪还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打粉”话务该当何罪,是诈骗还是非信?
原创 吴律宏 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
问题的产生
在电信诈骗中,存在一类型诈骗方式为先安排“话务员”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打粉(吸粉)引流”,劝诱不特定人员加入指定群组,加入群组后“话务员”即结束工作,后续将由其他公司、人员进行跟进。
从外观上,这与日常的“骚扰电话”十分相近,两者的区别可能只是在后续加入的群组中,群组人员是以诈骗为目的,还是其他“不构成犯罪”的目的。
但是不论后续是诈骗抑或真实引流,在前期“打粉(吸粉)引流”话务环节中,实际上话务员、组长抑或话务公司其他员工(以下合称“话务员”)通常并不知晓后续的具体操作及结果;其只知晓公司培训的话术、工作流程,甚至入职也是在正规招募软件上入职。
那么当后续诈骗团伙落网后,通常都会将“话务员”一网打尽;但“话务员”的行为应以诈骗罪共犯论处,还是仅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在实务中有不同观点,就此笔者结合该问题进行分析。
关于“话务员”可能构成诈骗罪的分析
若以诈骗罪的角度出发,实际上“话务员”处于的阶段应是诈骗罪的犯罪预备阶段;因为此时只是为诈骗犯罪实施进行着手,让潜在被害人进入到聊天群组,为后续可能实施的诈骗创造条件,并没有实施诈骗。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4起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典型案例(2019年10月25日)》的“二、谭张羽、张源等非法利用信息网络案”中,法院就认为“通过信息网络发送刷单诈骗信息,其行为本质上属于诈骗犯罪预备,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这也肯定了犯罪预备阶段的观点。
在实务中认定“话务员”为诈骗罪的法律依据通常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二款所规定的“利用发送短信、拨打电话、互联网等电信技术手段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诈骗数额难以查证,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一)发送诈骗信息五千条以上的;(二)拨打诈骗电话五百人次以上的;(三)诈骗手段恶劣、危害严重的。”
该条解释将“话务员”以诈骗罪(未遂)定罪,而非前述案例的“犯罪预备”;这是因为该条司法解释属兜底解释,首先仅在“诈骗数额难以查证”的情况下方能适用,也已经说明了“话务员”需要与后续的诈骗行为有直接关联,有意思通谋;其次“实施诈骗,诈骗数额难以查证”与“拨打诈骗电话”的规定已蕴含了在拨打电话时就具有主观诈骗意图,且电话内容应包括诈骗实施行为的相关内容。
因此,适用该司法解释以诈骗罪入罪的,应当有证据证明“话务员”与诈骗罪主犯之间存在诈骗的意思通谋,“打粉引流”与“诈骗”之间在时空上存在紧密联系。否则,“话务员”的行为至多只符合“诈骗罪犯罪预备”的标准,且由于不存在意思通谋,并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从实务角度出发,该条所规制的应当是“直接在电话中实施诈骗”的行为,如在电话中假冒公检法等诈骗,当电话拨通后就已经持续地进行诈骗,打电话的目的就是在即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取得钱财,若此时潜在的被害人没有上当受骗,则本次拨打电话便属于未遂,在法律解释上也符合诈骗罪的定义,以此认定诈骗罪属于合理。但若是类似本文提及的“话务员”,由于其在电话过程中并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则实际上并不符合诈骗罪的定义,不应当以此认定诈骗罪。
“话务员”可能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规定“利用信息网络实施下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一)设立用于实施诈骗、传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的;(二)发布有关制作或者销售毒品、枪支、淫秽物品等违禁物品、管制物品或者其他违法犯罪信息的;(三)为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发布信息的。”
“话务员”的“打粉”行为,在有证据证明后续实施了诈骗等违法活动的情形下,就符合了“为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发布信息的”的构成要件;如同时符合“情节严重”,就符合该罪名。
该罪名规定“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该条明确规定了“为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发布信息的”构成该罪,实际上蕴含如仅实施该行为的,就仅构成该罪名;只是在对诈骗行为实施多种帮助、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情形下,才会适用处罚更重的罪名。
例如,在“打粉引流”过程中,除以‘荐股’等名义将被害人引入上游犯罪分子微信群,还非法获取他人微信号等公民个人信息提供给上线,那么就同时构成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择一重罪定罪,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入罪。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1件检察机关依法惩治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典型案例》“鲍某等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冒充证券公司客服以提供股票咨询为名获取‘微信号四件套’案例中,检察院就是采用该逻辑,该案例具体内容为:为上游犯罪团伙‘引流’中,检察院认为鲍某等人为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提供引流帮助,以‘荐股’等名义将被害人引入上游犯罪分子微信群,同时符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构成要件。鲍某等人还非法获取他人微信号等公民个人信息提供给上线,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且属情节特别严重。根据择一重处原则,本案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该案的典型意义为:“吸粉”引流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上游关键环节,已形成黑灰产业链。成立公司、招募人员,形成较稳定“引流”团队,非法获取客户微信号并提供给上线,既为诈骗犯罪提供了帮助,又侵害了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同时触犯多个罪名的,应当择一重,依法从严惩处,从源头斩断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黑灰产业链条。
除此之外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8件个人信息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的“案例五、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人民检察院诉张某某等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中,法院查明“吴某组织‘吸粉引流’话务团伙10余人先后在宁夏青铜峡、湖北武汉、湖北鄂州租住房屋,冒充相关证券公司客服拨打客户电话5万余次,为200多个涉电信网络诈骗群‘吸粉引流’14130人”,最终二审法院认定“张某某等16人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维持原判”。也说明了纯粹的“吸粉引流”话务团伙只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而非诈骗罪。
根据北大法宝查询,截至2024年9月20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4年有402例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案例,其中大多数都属于“话务员”在网上根据话术从事工作的行为,此类大量案例实际上也足以证明了,按照指定话术打电话、拉进群,符合“为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发布信息的”,应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定罪。
“话务员”即便知晓后续可能发生诈骗行为也不代表被告人犯诈骗罪,因在诈骗罪实施过程“话务员”并未直接参与,没有在诈骗罪实施过程中有意思通谋,只是在犯罪预备阶段提供帮助;若以知晓后续发生诈骗行为来认定诈骗罪,实际上就架空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为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发布信息的”等规定,因为该条规定实际上就已经需要被告人主观明知其实施的行为是为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了帮助。
即便确因为“话务员”的打粉行为造成被害人损失的,也需区分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的缘由。若被害人的错误认知主要源于后续诈骗分子所虚构的事实,而非打粉过程中“话务员”电话描述的内容,则并非因为“话务员”的原因造成被害人的损失,“话务员”的行为并不符合诈骗罪的认定标准,即便被害人有损失,也不能以此认定“话务员”就是诈骗罪。
只有在有证据足以证明“话务员”与诈骗罪主犯之间存在意思联络、存在意思通谋,“话务员”的行为与诈骗行为在时间、空间上有紧密联系,已经超出了犯罪预备阶段的准备工作,直接参与到诈骗罪的既遂,否则对“话务员”不应以诈骗罪定罪。
//本文作者
吴律宏 ■ 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 |